不如不要重來了——從王家衛電影看香港末世憂鬱
- Chan Wei-Bing 陳薇敏

- 2020年4月5日
- 讀畢需時 11 分鐘
前言:是懷舊濫觴、還是未卜先知?
「不如我們從頭來過。」乃《春光乍洩》(Happy Together, 1997)中,何寶榮(張國榮飾)總愛對黎耀輝(梁朝偉飾)説的。兩人在愛恨交加的慾池裡血腥相殺,這句話,正代表著對於「忘記過去」、「重新開始」的渴望與想像。兩人一次又一次地如同猛獸般撕裂對方的肉魂,在傷口中癒合,又繼續劃破新的血口。懷舊、異地、回溯、膠著——此種對情愛、身份、地域等等的認同感缺失,實則長久以來作為王家衛電影美學的終極母題,反覆拷問,卻不得而知。
70年代末,「香港新浪潮」中,超過60位導演初次登場,展現了作者電影的新局面。在此之前,香港以製作武俠片為主,出口世界各國;在中國仍處於文革時期的整個時代環境下,甚至致使外界以為香港電影即是中國電影。如果說藉此創造出了「以忍耐、禁慾主義和徹底的自我修煉為代表的理想中國人——像李小龍的電影,若能代表香港電影的世界化(globalization)方向的話,那麼,年輕一代們則開始轉而關心直接拿出自己所屬的社會和文化來討論的廣東話電影,則可以說是和本地化(localization)有關的部分」。[1] 而王家衛則落在了第二代浪潮的座標。
然而綜觀其創作史,王家衛固然是以較為隱式的策略回應此課題。從1988年的《旺角卡門》(As Tears Go By, 1988)起,王家衛的審美浪漫主義式懷舊情懷,為我們建構出他的電影世界觀。然而,如果所謂「香港電影」是由香港電影工業的主流運作模式,以及主流香港觀眾的口味去界定的話,從敘事結構、畫面構圖、鏡頭調度、題材、市場定位等方面來看,王家衛的電影都明顯地不太像一般的「香港電影」。[2] 將其放置在後九七焦慮、殖民政治的普遍華語電影論述下,則會發現:王家衛電影鏡頭下呈現出的香港時空,並不是當前的香港,而是對一個過去的香港的懷念與再現。[3] 王家衛對於「時間」的執拗,從《阿飛正傳》經典的「那一分鐘」,到《2046》明確標示出一個遙遠的未來,這些自我身份的追尋、漂泊離散的孤者,即是反映在香港、中國與整個東亞處境上,「家」究竟在何方?
由此,在現今這個無論是政治、還是歷史主體皆劇烈分裂的動盪時代,香港人的歸屬感再次成為流血抗爭的絕望悲鳴。王家衛的電影攝影、剪接美學,是最為人討論的。然而跳脫此論述滿載的脈絡,本文意欲從王家衛的敘事方法出發,扣緊每一個可能的母題,藉以回看「另一種香港論述」:不武俠、不情色的——更多的,是自我詰問:如此沉溺、耽美、濫觴,在這個時代,我們還需要一個王家衛嗎?又或者,其實我們亦是在無法掌控自身命運的無奈之中,一步步走到了一種王家衛式的、香港末世憂鬱?
(一)旺角卡門、阿飛正傳:我為命運戰鬥,或低鳴
1988年,《旺角卡門》公映,電視台編劇出身的王家衛,成為受人矚目的導演之一。在第二部《阿飛正傳》起,充滿個人特色的敘述手法,宣告了一個明星般的作者導演誕生。《旺角卡門》則如同遺世孤兒般,在論述的經緯之外。在製片人、妻子陳以勒的牽線下,王家衛獲得了一大筆資助,得以開拍此片。透過拼貼式的快速剪接、大量配樂及音效使用、手持攝影機、濃郁色彩(以顏色代表寓意與場景)——我們似乎還未真正找到一絲絲「王家衛式」的蛛絲馬跡;歸屬於八十年代中興起的江湖/英雄電影類型,《旺角卡門》則相對直截簡練。
華(劉德華飾),黑社會大佬;烏蠅(張學友飾),他的跟班。處於對立的,是開場的肥九、Tony哥、甚至是結尾時,背叛社團的大口基,以及警察。這些人中,有同門反目成仇、不睦的,亦有同屬一個世界(黑社會、旺角黑夜),卻仍必須仇視彼此,藉以尋得上位的機會。而表妹娥(張曼玉飾),則帶出另外一條軸線——在鐵漢之內的那份柔情。江湖以外,還有愛情。華終日徘徊於這兩種世界,乃至他最後只可選擇其一的命運。實現愛情的場景只有大嶼山,相比於腥風血雨的旺角夜街,帶出了「城—鄉」之間的對立:在甜夢般的情境裡,「改變命運」——它並不真實。
華和娥的關係,抒情而浪漫。江湖人物是夜間的動物,片首華家的一場戲有生動的處理:娥早上到來,他卻一直蒙頭大睡。難免引人聯想:娥可會是華逃避現實而生的夢中幻影?《旺角卡門》作為王家衛從編劇到導演的「華麗轉身」,鏡頭下,人物的卑微不堪、夾縫中生存的社會狀態,這些都只有在「華麗」的襯托下,才更顯其「頹敗」之美。生活的窘迫和暴力感,一場一個衝突,發展下來,壓力不斷積累,絕望的調子不斷加深,終於上演華和烏蠅雙雙斃命的結局。[4]
《旺角卡門》的悲壯淒涼、人物殞落,跟接下來的第二部作品《阿飛正傳》如出一轍,令人惋惜。這回,王家衛不再像《旺角卡門》般走商業與藝術的鋼索,而是執意只拍自己相信的東西,其義無反顧的態度,當真可貴。而影片最令一般觀眾無所適從的,相信是它只有人物,卻沒有完整的故事或情節。影片基本上由幾名主角的聚散構成,其敘事方法,也是通過母題的重複、多重敘述者的旁白與攝影美學的統一所串連。[5] 而「時間/時鐘」的主題強調,更成為此片最經典的發展脈絡。
《阿飛正傳》(Days of Being Wild, 1990)的誕生,重構出那充滿懷舊遐想的六〇年代。美國著名文藝批評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提出:第三世界的文本「必然」會以「國族寓言」的方式投射出一個政治向度,即那些看起來似乎是講述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以國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總和第三世界的公共文化與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有關。[6] 由此,亦可將這樣的時空背景理解為是由個人的偶然所衍化出來的一種集體必然。
本片創作於1990年,正好回應了九七回歸前的香港焦慮——無腳的鳥仔,「旭仔」(張國榮飾)這種無家可歸的敘事構造,離不開1980年代末,香港的「九七」和「六四」情節。在較為動盪、劇烈變革的轉型期中,當個人、地方、國族的三重命運成為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可避免的議題時,這樣的文本,即是更有可能以「寓言」的方式投射其政治意涵。[7] 旭仔尋母,是一個追尋過往歷史的旅程,深刻地預示了香港當時的社會背景。一個久經英國管轄的香港,在商業經濟發展、意識形態等皆與中國具有差距的明顯下,「個人」在「國家」面前,又該如何自處?旭仔的「尋根」,無非是將精神的流浪、肉身的漂泊,轉換為命運的失序乃至無序狀態。相較《旺角卡門》華的戰鬥,旭仔在這裡只是作為一隻無腳的鳥,動物般地等待著自己的悲慘宿命,時而絕望、時而低鳴。

(二)重慶森林、墮落天使:失語者的意象
《重慶森林》(ChungKing Express, 1994)是在《東邪西毒》做後期剪接時完成的。整體而言,氣氛輕鬆、自然,更奪得了多個重要獎項。在王家衛的電影裡,常常沒有確切的歷史或時代,即使《阿飛正傳》似乎講述著一個六〇年代的故事,仍然是抽離、淨化、想像中的六〇年代。這是一個極為封閉的電影世界,所有人都被禁錮在一個永恆不變的生命狀態裡:等待女友歸來的警員663(梁朝偉飾)、阿菲(王菲飾)與她那首California Dreaming、警員223(金城武飾)與被標上日期標籤的鳳梨罐頭——這些總是在同樣的記憶裡反覆折磨自己的人,膠著、停滯;對比歌曲中「加州」這個陽光明媚的地方甚是譏諷。
《重慶森林》裡,那些以數字代稱自己的人,如同在這個淨化、抽離的環境裡,對自身迷茫的失語者。這些代號,象徵著被量化的人物生命、常規、無名。沒有個人情感的223、663,在這些自我防衛心理、自給自足的空間裡,他們過份低調的角色,卻有著極為豐沛的情感。若說王家衛的電影是香港人的「真實」寫照:沒有歷史感及豪情壯志,活的世界很封閉,但卻有張不出口的感情,[8] 稍不留神,則在這樣的時代、地點中,被感動得死去活來。阿菲工作的場域——三明治漢堡快餐,這樣的午夜速遞,即是在一個普遍的日常香港中,呈現一種被異化的生活方式:當城市安穩沉睡,我則在時間(速遞)沼澤裡,繼續無能為力。
將人類數字化、歸檔化,在《墮落天使》(Fallen Angels, 1995)中,更是推到了極致。天使1號、天使2號、天使3號、天使4號、天使5號,如同在這個世界裡,我們都是被複製出來的生命般,是世界的客體,而非主體。此片的故事主線是黎明和李嘉欣,也就是天使1號跟天使2號。兩人雖然在同一間屋子裡出沒,卻從來互不相見。第二條軸線,則是天使3號的金城武、天使4號的楊采妮。金城武是個啞巴,孩提時代因為母親逝去而拒絕說話。我們必須明確指出的是:天使3號並非不曾擁有過語言能力,而是有意識的失語症。[9]
在《墮落天使》中,透過他的獨白,我們知道他的母親是俄羅斯人,父親那口俄羅斯台語,更在此片中帶出更豐富的語言情景。與《阿飛正傳》失去母國的旭仔一樣,金城武是「失去母語」的人。俄羅斯代表了母親的所在地,如同一個遙遠的幽靈、一個幻想之地、一個不可能卻也不可取代的異鄉。金城武從未踏足過,作為混血兒的他,早就註定了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自我分裂的宿命。這個巨大的裂痕,更是以作為台灣移民到香港的某種空間裂痕。人類真的有辦法「落地生根」嗎?金城武在新的移民之地,他拒絕說話,消極地拒絕再對這個世界或自身記憶寫下任何註解。他放棄語言,也就放棄了「證明自己是誰」的權力。
然而《墮落天使》的異質,卻在於一、以獨白呈現自身想法的失語者;二、在粵語電影中,金城武那口台灣腔中文。「自從5歲的那一年,我吃了一罐過期的鳳梨罐頭之後,我就沒有再講過話了。」但什麼是「說我的語言」(speak my language)?我們如何說一種雙唇緊閉不能出聲的語言?這個要說的語言和失去的語言,是否為相同的語言?[10] 最重要的,是語言,僅僅是聲音的表達嗎?香港在語言的課題上,一直是複雜的。1997年回歸以後,中國所講的普通話,更是以一種異質物的方式,重擊香港本土。怎樣的語言,是香港的語言呢?我們必須理解的是:語言作為人類文明的起源,失去語言的人,即如同失去生命根源的人。被剝奪語言權力的人,即是被剝奪了自身歷史的人。當我們無法講述自己,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記憶文明。
(三)花樣年華、東邪西毒:記憶的奴隸
《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 2000)無疑是王家衛電影中,將「曖昧」的美學表現得最為極致的一部作品。其創作靈感取自劉以鬯的小說《對倒》,更上承《阿飛正傳》,下續《2046》。此片表面上是關於婚外情的故事,實則表達了王家衛的中年情懷與時代記憶,借一男一女在越軌行為與意識上的掙扎和遊移,寄寓他對那個年代的風物景觀和情感模式無限的依戀與沉溺。[11] 事過境遷,蒼涼於此,此片闡釋了六〇年代香港與三〇年代上海風華,那些上海國語時代的曲目拼貼,周璇所唱出的,無疑是對已逝的追憶:「花樣的年華、月樣的精神⋯⋯多情的眷屬、圓滿的家庭⋯⋯」
1966年,梁朝偉在柬埔寨吳哥窟的一座寺廟,對著樹洞講述自己的秘密。對於失落的年代記憶的追思,在於王家衛曾經說過,電影選擇在1966年結束,是因為這個年份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代表了一些東西的終結和另一些東西的開始,而他之所以把電影結束的場景帶到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以殖民者的身份訪問柬埔寨,是為了隱喻香港的殖民歷史。[12] 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了這樣的字卡:「那些消失了的歲月,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失的歲月。」
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中,中國共產主義份子製造政治衝突。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撞擊,催生了不少的反殖民示威與暴動。港英政府在之後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試圖緩解民眾的情緒。香港邁入經濟轉型,以致於所謂「舊有的價值觀」更一步步地被徹底瓦解。或許從這段歷史去看,《花樣年華》所闡述的,更是一個對於殖民者的「曖昧」狀態:我究竟是誰呢?蘇麗珍(張曼玉飾)在「那張船票」以後,返回原來的地方。然而物似人非,這份惆悵,也就是在一個急速變化的香港中,中年份子的適應不從。他們太熟悉過往,要怎麼向前?
關於記憶的母題,在《東邪西毒》(Ashes of Time, 1994)卻已經小試身手。此片以類武俠、實則文藝的方法,帶出了英雄的寂寞。片名為「時間的灰燼」,但面對一大片沙漠,空間卻在日與夜的交替中,看不出任何差異。大量的主觀鏡頭與碎碎囈語,營造出時空錯置的效果。我們在回憶鏡頭與當下之間渡步、甚至迷路:「沙漠之後還是沙漠」,更添了人物的蒼茫、無力之感。或許人在迷惘以後,將會拋下那些令他真正痛苦的記憶,然後長大,昂首闊步。
結語:2046真的仍未到來嗎?
在《2046》(2046, 2004)中,戲中公寓內的2046與2047兩個房間,即是變與不變的空間;更和失落了的過去重新交接。中國政府曾經承諾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的五十年不變。從1997年算起,2046就是五十年不變的最後一年,也是不變的極限。換句話說,2047就是變的開始。[13] 然而這個寓言,卻已經在近幾年的雨傘運動、反送中示威抗議中,一一瓦解。香港正處於一個自我分裂、甚至集體被消失的困境,從前主流所認為的王家衛世紀末憂鬱,正預言似在香港本土發生。從《旺角卡門》、《阿飛正傳》那些無法掌控自身命運的人;《重慶森林》、《墮落天使》那些失去語言與記憶文明的人,到《花樣年華》、《東邪西毒》的追憶似水年華,我們可以確信的是:正因為已經失去了,所以只能剩下緬懷。
王家衛的電影母題,不斷地涉及到身份、記憶、語言、地域的相互交疊。那些離開出生地的人、或是尋找出生地的人。一直沉溺在自己是誰的人、或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不斷說話(旁白)的人、或是失去說話能力的人。被記憶折磨的人、或是失去重要記憶的人。這樣的對倒與重複,凸顯了「香港」的矛盾性。畢竟近七十年來,香港人的身份不時在改變,從開埠最初的難民身份,到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市民身份,到九七後至今的中國公民身份,一次又一次的身份改變,使香港人對人對事的價值觀也在不斷改變,從而亦影響了整個社會的人事變遷。[14] 王家衛似乎是更早地處理了五十年的這個寓言,將其創作脈絡攤開解剖,則事實令人感到絕望。那些耽美,只不過是一種經由絕望所帶來的浪漫想像、自己給自己創造希望。所以我們必須捫心自問:2046,真的仍未到來嗎?
不如我們從頭來過?端看如今流血事件,所有的主體只能在這個宏觀的「大中國統一」論述下,淪為被毆打的客體。2020年的香港人,已經失去了他們的語言、記憶、身份,甚至是生命。在連月的抗爭中,超過20%的香港人更是罹患了憂鬱症等情緒,對於當下及未來皆感到憂心忡忡。藉著王家衛式的末世憂鬱,我想絕望地說一句:不如不要重來了。
[1] 林春城(Choon-Sung Yim),〈論香港新浪潮電影〉,《華文文學》(廣東:汕頭大學,2010),頁84-92。 [2] 邱加輝,〈影像香港:王家衛的八部電影與六個香港〉,《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 [3] 劉永皓,〈跨界追尋、南洋迷離、懷舊香港——王家衛電影中的跨界敘述〉,《小電影學:電影複像、轉場換景與隙縫偷渡》(臺北:左耳文化,2010),頁53。 [4] 劉嶔,〈《旺角卡門》,鐵漢與柔情,江湖與愛情〉,《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5),頁119。 [5] 李焯桃,〈《阿飛正傳》,世紀末的遺憾〉,《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5),頁123。 [6]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986. [7] 袁夢倩,〈創傷書寫、香港身份認同與國族寓言——重讀香港電影《棋王》〉,《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8] 家明,〈《重慶森林》,場域遊移與數字戀愛〉,《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5),頁183。 [9] 黃志輝,〈《墮落天使》,告別江湖,輕裝上路〉,《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5),頁188。 [10] 劉永皓,〈王家衛《墮落天使》中的失語現象——失去的語言與多出的電影語言〉,2005。 [11] 洛楓,〈如花美眷——論《花樣年華》的年代記憶與戀物情結〉,《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5),頁213。 [12] Tony Rayns, “In the Mood for Edinburgh”, Sight and Sound, 2000, pp. 17. [13] 邱加輝,〈影像香港:王家衛的八部電影與六個香港〉,《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 [14]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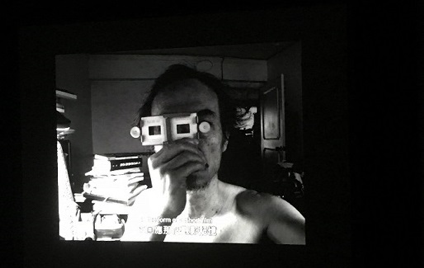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