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沉的旁觀者:冷戰與香港身份認同——以陳果《紅VAN》為例
- Chan Wei-Bing 陳薇敏

- 2020年4月5日
- 讀畢需時 6 分鐘
二戰結束後,以集中在美國、蘇聯兩大陣營的歐洲中心主義式的冷戰研究,對於想要了解香港的處境實則是有困難與距離的。事實上,在冷戰尚未形成前,亞洲經歷長期的殖民主義跟民族主義運動。在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運動間,各地域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相互交織;而這跟冷戰的意識形態、香港的地緣政治等等,又逐步演變成另一種樣貌。為了避免將「冷戰」作為足以解釋一切的宏大背景,本文冀望從東亞視角出發,回看並拆解冷戰結構,進而梳理出一條脈絡;以及最核心的,是香港電影產業究竟如何在這樣的歷史、政治經驗中自處?又迸發出怎樣的火花?
香港的歷史處境
在東亞,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到日本軍國體制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方案,「國族」與人種差異,一直都主導著政治框架跟其策略基礎。而以香港的冷戰經驗來說,若是回溯到冷戰前的中國民族主義,即:十九世紀末,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就曾在香港留學、建立現代民主主義,並組織推動民族主義革命下,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民族想像,便開展出難以分割的歷史狀態。
而孫中山所推崇的理想,並非所謂的反西方帝國,而是反滿清帝國的、漢人民族主義革命。這時候的香港已在英屬殖民統治中,在孫中山看來,英國其實向腐敗的滿清帝國示範了先進的社會管理方式,以致認為那是有進步意義的殖民統治,並由此嫁接了對應的理想性。香港,一方面作為割讓給外國人的地方,是中國民族的羞恥;另一方面,又實際上是對外開放的——讓不同力量相互連結、各自角力的自由空間。從無論是移民、移工或是其作為經濟城市的定位⋯⋯如此幾個面向看來,亦就奠定了香港在歷史處境上的複雜性。
「視域不是一種特定的思想,或指向自我的在場(presence)。它賦予我一種中介,讓我抽離自身,但同時由自身內部(而不是存有的面前)處身於存有(Being)的裂縫(fission)中,這個裂縫的終站,正是我回到自己之處。」(梅洛﹣龐蒂 1964: 186)
在葉蔭聰的〈旁觀者的可能:香港電影中的冷戰經驗與「社會主義中國」〉(2009)一文中,葉式提出了香港作為某種「旁觀者」的歷史位置。以笛卡爾的「我思,我在。」,建立了「思維與存在」為同時出現的相關論述,從而開展出胡賽爾、梅洛﹣龐蒂等人對「我」與主體性的觀念辯證。而具有空間緯度的物質性身體,與建立感覺的經驗性身體,在兩者的縫隙上,從而產生「生命的主體」。
何謂「旁觀者」?或許即是某種抽離與無法靠近:「身體」身處其中,卻無法「經驗」,更沒有任何「生命的主體」。而將它比擬香港置身在目前的政治處境中,那些無法擺脫、卻也無法理解的,便是身份(體)上的「無法認可」。「香港」是什麼?「香港人」是誰?有無「香港性」?香港這個美麗的旁觀者,其模糊與曖昧的定位,在對歷史與政治的「觀看」中,形成與他者一段恆久無法克服的距離。

作為方法的可能性:後殖民
「香港的故事一向難說,近年香港本土文化更一再被指快將(已經)死亡⋯⋯」(朱耀偉 2015)
所謂香港本土,本質上即是混雜而非單一的。在朱式〈香港作為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2015)一文中,指出:「香港不再是香港,因為以往香港在中國與世界之間顧盼生輝,本地在國家及全球之間左右逢源,如今中國擁抱全球化變成世界,香港亦因此無所適從。」從前的香港,在中西世界之間,又在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夾縫中自我書寫,也在全球與本土之間作出自我論述。然而1997年香港回歸,香港人面對如斯困境,唯有如同陳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簡稱:紅VAN)一片,眾人對於「獅子山下」的救贖嚮往,從而麻醉香港人、麻木香港意識。
《紅VAN》為陳果於2014年的作品,改編自網路作家Mr.Pizza的同名小說,集懸疑、驚悚、科幻等元素於一體。而片中隱藏的政治隱喻充滿爭議性,在籌備之期,陳果以「不能干涉他如何改編」為前提,醞釀此長片,更與監製直言:「作為導演,倘若沒有我的角度,這作品就不是我的了。」《紅VAN》講述一台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在離開了獅子山隧道後,發現所有人和車都消失。剩下的十七人中,有人離奇死亡、有人遇到光怪陸離的事;餘下的人設法解決眼前的問題,祈望「回到本來的香港」。
而紅VAN作為香港的特別交通工具,同時也是電影的靈魂。「小巴」文化,乃是在鐵路尚未發達的年代而興起的。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中,中國共產主義份子製造政治衝突。期間,有一種「白牌車」,即是非法載客的私家車與小型貨車(即是VAN)遊走新界接客,並躲避警方掃蕩。暴動那年,公共巴士服務癱瘓,白牌車到街上接客,而為了減少市民的交通運輸問題,「非法VAN」在後來更成為合法載客工具。「小巴」在香港,於是象徵著英國殖民政府的遺緒。
從《香港製造》開始,陳果即已開展出對於「香港 ﹣中國」的電影論述。他的「後九七」電影,常常探問香港人的焦慮與躁動。陳果抗拒將《紅VAN》定調為「政治電影」,而認為它僅是一部有意識的商業片。然而,性的、暴力的、不語的,皆是他在無論是妓女三部曲或這部「商業片」中,一一鎖定的母題。
在《紅VAN》裡,眾人如同「都市漫遊者」(Flâneur)般的形象,與人群若即若離,卻又困在同一個空間裡,共同形塑香港的城市觀察。眾人在「那夜凌晨」這個被永恆固化的時間緯度裡,讓「當下」與「未來」皆變成不可能的。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消失了,餘下的人雖然試圖團結,卻又合力殺死了一個人。崩塌的道德觀,如同崩塌的香港核心價值,一切看似正常,卻又詭異如魅。
後殖民研究於七〇、八〇年代在西方迅速勃興,至八〇年代末,這股批判浪潮開始席捲亞洲。兩岸三地因為不同的原因,促使後殖民研究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徑。而這種「後學」(post-ism)式的主張,在「後九七」焦慮中,更是成為了香港人尋找本土身份認同的重要論述。香港是個典型的殖民社會,或許香港人是「毋需」擁有記憶的,如同《紅VAN》中,那些(被)消失的親屬、(被)消沉的求生者般,香港人突然意識到:除了「獅子山下」的精神救贖外,腦袋早已一片空白。
「六、七十年代中同舟共濟、刻苦耐勞、不屈不撓的獅子山精神,是一種以集體為先,強調為家庭而付出的精神。加上當時香港由轉口貿易主導轉為工業主導、大量人口南移、大量發展空間的背景,只要有手有腳,安分守己,當時的人就能養活自己,甚至是一家幾口。如果肯放手一搏,甚至有賺一桶金的機會。」(香港01:這個名叫獅子山精神的牢籠)
香港故事究竟要如何說下去?在如今(被)消沉的政治經驗中,香港意識該如何甦醒?或許為了生活,我們都必須對過去選擇性失憶、並且展望那些看似怪談的未來。而若再從東亞視角看香港的冷戰經驗,在1979年,從鄧小平訪問美國起,中國與美國便已在某種程度上進行冷戰和解。中國開始以「國家主義」建構她在亞洲權力的中心位置。在大環境和解、內部持續夾攻的雙重結構下,殖民權力卻得以在香港維持。
任何鼓吹社會改動者,都被指責為受到「西方帝國反華勢力」的影響——「冷戰」,仍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實在很難判斷哪些影響對香港產生了作用,皆因冷戰的任何一方都未曾完全主宰過香港的政治、經濟跟文化發展。但兩種意識形態都同時在香港出現,令香港人有著雙向辯證:異質且混雜。這種獨特的經驗,它的代價,就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內在矛盾。
不完整、半個世界的香港,將眼光放到現在,依舊是被殖民的歷史鬼魂所打壓。對於「我思,我在」、對於身體與意識,或許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這些歷史(意識)所銘刻在「香港」這個(身體)上的傷痕⋯⋯這一切何時才會到頭?「獅子山」還在眼前嗎?「家」在何方?藉以這部《紅VAN》中的一句台詞,或許便是最好的回應:「我們的香港,已經不存在。」
參考書目
葉蔭聰(2009)。〈旁觀者的可能:香港電影中的冷戰經驗與「社會主義中國」〉,《文化研究月報》。台北: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陳光興(2001)。〈去冷戰:為什麼大和解不 / 可能?〉,《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
羅永生(2007)。〈香港殖民(去)政治與文化冷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朱耀偉(2015)。〈香港作為方法——關於香港論述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張英進(2007)。〈反對修正:戰爭時期的香港電影與地域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史書美著、吳建亨、劉威辰合譯(2016)。〈何謂華語語系研究?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吳若慈(2008)。〈「身體」與「意識」概念在梅洛龐蒂「肉身主體」所獲得新的意義視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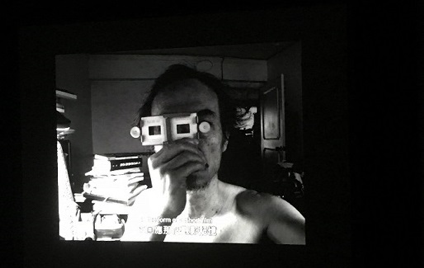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