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未來:電影政治與記憶的問題
- Chan Wei-Bing 陳薇敏

- 2020年4月5日
- 讀畢需時 8 分鐘
在對馬克思的研究中,我之所以重視「幽靈性」的問題,不僅僅因為馬克思說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在歐洲遊蕩的幽靈,也不是因為哈姆雷特回來進行埋葬的工作。(⋯⋯)是因為「幽靈性」的問題,今天似乎成為理解技術、交流變革方法(電視、網絡、電話、手機等)——它接受物理空間和向地空間。「幽靈性」的概念對於分析我們時代的這些技術、新技術的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雅克 ·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2003)
一、阿比查邦的幽靈式書寫
幽靈,意味著某種顯現的、可見的死人。「可見性」作為幽靈顯現、乃至使痕跡成為可測量的歷史時間之必要條件,似乎勢必與「影像」這類可見/再現物同源。「可見性」總會在未來的道路上出現,而德希達認為「鬼魂」卻是不必然可見的,意味著事件的不可預見性、歷史的時間——那些再也不可追溯、已然消逝的。對於這兩種緯度的顯與隱,我試圖論證的是:阿比查邦如何以他獨特的幽靈式(性)書寫,將它們體現在自己的影像藝術裡?
宗教,在歷史時間上具有推動、前進的意義。神話、傳說,乃是人類渴望及其適當之想像形式的具體表現。(劉秋固,1998)將想像轉譯成能指,是人類解釋歷史現象或歷時經歷的集體創作,反映出人類意在與自然相抗爭的心理歷程。而這種將神話、傳說轉換為無論是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或是《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2010)裡,那一張猴靈顯現的照片等等,都是在遠古與已逝的時間中,企圖尋找人類生命的原初與其型態。這種對生命的終極關懷,與崇高永恆的形象化、如同木乃伊裹屍布被封存的一張臉;更是一張歷史面孔般,似乎即是某種承襲自巴贊〈攝影影像的本體論〉,阿比查邦以其對泰國在地進行影像書寫。
在南傳佛教未傳入泰國前,其在地文化便是結合源自印度與中國的迷信信仰,形成獨有的泰文化中的萬物有靈論(泛靈論)。「泛」,即是無所不在。長久以來,在神話思維中,「萬物有靈論」(animistic)所形成的思想脈絡,是人與宇宙萬物在有靈的信仰下,彼此可互相滲透、混為一體。以這樣的神話思維趨近理解阿比查邦的幽靈式書寫,便不難發現活人與非活人的(如鬼魂),常常具有類似的相互滲透性。死去的妻子,如同活人一般照看病重的波米;活著的波米,如同鬼魂一般在歷史的、記憶的時間中自由行走。
阿比查邦的幽靈式書寫,不僅如常被論述的「使鬼魂可見」,真正超現實的,是讓活人被轉化為活死人般的視點⋯⋯這些具有時間與記憶穿透力的病體,往往皆是未死的、未完成的鬼魂。一種游離自當下、卻又仍在當下的病體;因為歷史與生理的雙重病徵,進而擁有非人(non-human)、超驗(transcendent)的感知力。這些似鬼魂的人、似人的鬼魂,在成為歷史的言說者後,現實透過什麼而證明?即是語言所喚起的話語的現實。創傷的先驗主體與語言的現實互換意義,突變並實踐泛靈論中、共感共知的複雜體。
二、凌遲考:記憶的政治
「在田野現場」(being there)被視為一種風景明信片式的經驗,(林徐達,2012)而「幽靈」作為製造傳播、印跡、技術的形象,在陳界仁於《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2002)中所提出的「被攝影者的歷史」:1904年的法國士兵體現存有、此曾在(dasein)以及在田野現場之指涉經驗。成為客體的對象被認識、被詮釋,甚至在後來被製作成明信片在歐洲流通,成為被閱讀的他者、一道可供眼睛視覺觀視的風景。藉由「攝影機」與「被攝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捕捉這些跨文化、甚至曾被視為中國是「野蠻殘酷」的證據(陳界仁,2002),真正滿足了對於古代東方的民族想像。
陳界仁藝術家以佛教中的「回向」闡釋凌遲酷刑的歷史照片:強調個人從修行中獲得體悟與功德、需與眾生分享的態度,其精神本質意即與他者連結、對話。凌遲受難者的「微笑」,作為技術的痕跡、歷史的幽靈,因為成為一張照片,以致開啟與未來潛在的觀者溝通、對話的可能性。這個「幽靈」的影像再現過程,呼應德希達所說的「幽靈性」(董冰峰,2019);更讓我們在現實問題轉化為美學行動的過程中,重新發掘圖像背後的歷史。或許正因為重新理解現實與真相,也讓我們(觀者)猶如能在時間中行走自如的鬼魂——每個人都(將)是鬼魂,這即是歷史給我們的命運。
從法國士兵到未來觀者、從機器之眼到人類之眼,所形塑的,是技術幽靈賦予的「目睹的力量」(the power of witness);並仿佛透過陳界仁的美學行動,反轉記憶的政治。或許在一百年前的明信片上,我們可以探問的是:西方的觀者們究竟如何理解這些遠在異地的凌遲照片所帶來的具體意義?這個異於自身文化的行動,在成為圖像象徵後,生人的痛苦經驗被複製生產——如此獵奇的影像商品,究竟是如何成為他們視覺經驗中的異國情調,甚至形塑出對東方抑或中國的記憶政治?這些充滿西方殖民意味的圖像生產、視覺霸權,在陳界仁提出「被攝影者的歷史」並轉化為二十二分鐘的作品後,過去的歷史現實被延異為一種去殖民、去視覺霸權、甚至是去記憶政治的再詮釋;或許就如德希達所斷言的那般:根本不存在終極的、唯一的思想與意義。
無論是阿比查邦或陳界仁,皆是在避免將歷史看作一個已經被整合、現實等於真相的世界;避免同一化,而是把這些影像事物引向無限的信息符號(signe)(朗西埃,2007)。他們對歷史現實進行去熟悉化,這樣的創作方法學,將「詮釋」與書寫權力敞開,並朝向某種持續進行中的行動,是現在進行式,而非過去式。歷史的事件永遠能被時間的進程清算,並試圖找出那些存在於「意義的意義」。阿比查邦透過與超現實主義的並置,將歷史創傷轉化為病理意象;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有別的,更是阿比查邦的逆向操作:波米叔叔重返洞穴,以期找到生命的原初。柏拉圖所主張的外在世界的理性文明現實作為人類的希望,似乎對阿比查邦而言,更趨向於真正的現實(真相)永遠是非理性的——槍彈、屠殺⋯⋯
倘若連結至陳界仁所考究的凌遲酷刑與攝影真相,更是對外在世界、光即是真相的反撲。因為「現實」的藏身之處,是暗處、是洞穴;真相,正因為其不可見性,才更有真實性可言。這些不可見的真相,豈不正是「鬼魂」般的存在?阿比查邦以幽靈式書寫歷史的鬼魂、以可見論證不可見;陳界仁在可見中,則映照其背面:那些被看的。如同照片作為「曾經」,這時卻神奇地走入自身的「未來世」(afterlife)般,以現實逆轉現實、以歷史證明歷史。

三、後人類作為出口?
無獨有偶的,是無論阿比查邦、陳界仁或是陸揚,皆反映出宗教力量所帶來的「未來世」、「過去世」之想像,如同某種彌賽亞時間般,更是以影像作為時間與歷史的彌賽亞,匿藏著意欲得到超脫於當下的救贖的終極渴望。在《陸揚妄想曼陀羅》(2015)中,陸揚以對於身體政治的去熟悉化、中性化,宣示「新人類」的到來。這些沒有性別之分的無性人,僅僅做一個人類,再無其他。而在「後人類」的論述中,其原意並非超脫或唾棄人類,而恰恰是要在深入時代境況的前提之下,質疑以往那些既成的人類本質,進而重新審視人類本身。
我們是否真正人類過?人類的有機體,何嘗不是一部最最精密的機器?或許可以做出一個虛假的預設:其實,人類從來都不是傳統人文主義所虛構出來的那個「主體」,或者說,人,只有作為寄生於、遊蕩於機器之中的「幽靈」(ghost/ specter),方可真正觸及自身的的真正存在。(姜宇輝,2017)我們這些機器中的幽靈,正是德希達闡釋意義上的「幽靈性」。或許身而為人,本質而言,從來都沒有逃脫過機械般的基因複製、文化意義與意識形態的複製,更不用說在對於身體改造(化妝、修容、整容)如此便利的易容時代⋯⋯人,已經是技術痕跡的表徵;人,即是幽靈。
《陸揚妄想曼陀羅》,首先意圖掙脫與顛覆的,就是「女性身體」如何在長久以來被賦予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與現實意義。成為了「類人」後,亦超脫死亡的、神性的觀念,藝術家陸揚主張一種自然身體與技術虛擬相結合的「化身」,更預示並期許著新物種的到來。在那個新世界裡,所有舊有文化與陳舊現實所帶來的身體/心靈傷害都將煙硝殆盡,以長久盛行的東方宗教的輪迴、轉世理念與當下急速發展的基因複製技術的烏托邦想像融於一體(董冰峰,2019),重塑一個更值得期待、更友善的世界觀。
而在阿比查邦與英國演員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合作、預計於2020年發行的電影《備忘》(Memoria),阿比查邦以睡眠時腦中猶如槍聲巨大聲響為癥結,開展出記憶與夢境的再一次對話。那個存在於腦中的世界,透過洞的窺看,得以被察覺。或許這部身體變異與地緣政治相互辯證的電影,亦開展出類似「妄想曼陀羅」般的後人類新物種主張:一種極具未來意味的期許。曼陀羅,在佛教中,意即壇,是諸佛聚集之地,也是能量的核心。人的腦袋,可謂即是人體這部機器的曼陀羅。我們究竟是誰?或許經過一場腦袋異世界的旅行,正好回應了這個痛徹心扉的現實問題。
長期以來,經歷視覺霸權與視覺殖民的亞洲影像藝術,如何劃破僵固的意識形態癥結,如同董冰峰在文末所言「成為一種祛魅的動能藝術」?而西方與非西方的歷史癥結,在槍彈、屠殺的非理性中,不僅僅是視覺,更多的是歷史所帶來的地理與生理創傷。這或許是地緣政治為何成為阿比查邦電影中恆古的母題;而攝影(機)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影像永遠是某個東西的影像,(讓 - 路易 · 鮑德里,2005)更永遠是現實的影像。無論方法是否寫實,影像所證明的是現實作為攝影機的參照物,現實在鏡頭前,影像才得以存在。當那些歷史成為影像,那些視覺中被延遲的刺點,在成為真相的所指後,未死的鬼魂也就完成它的使命,終於是時候真正成為一抹死去的鬼魂。無論是波米叔叔、凌遲受難者的微笑、抑或陸揚用新媒體藝術給自己架設的靈車,都在回答現實世界與影像意義的幽靈宿命論後,以成為鬼魂來終結時間的進程。
我將要告別了,因為我已把話說好。
參考書目
杜小真、张寧(2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頁73-86。
林徐達(2012)。〈論詮釋人類學的修辭轉向、當代批評與全球化挑戰〉,《文化研
究》14期。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姜宇輝(2017)。〈“未来属于幽灵”——在“后人类”的影像之中重拾叙事时间〉
,《当代电影》2017年11期。北京:中國傳媒大學。
孫松榮(2018)。〈影像召喚術:記憶的電影、失憶的歷史〉,《藝術家》519期。
臺北:藝術家雜誌社。
雅克 · 朗西埃(2007)。〈電影的眩暈〉,《寬忍的灰色黎明:法國哲學家論電影》
。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董冰峰(2019)。〈幽灵、类人、幻像:亚洲影像艺术中的自我反射〉,《世界美
术》2019年01期。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劉秋固(1998)。〈莊子的神話思維與自我超越的文化心理及其民俗信仰〉,《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5期。臺北:中央研究院。
羅蘭 · 巴特(2011)。《明室 · 攝影札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讓 - 路易 · 鮑德里(2005)。〈基本電影機器的意識形態效果〉,《凝視的快感:
電影文本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18-32。
Daniel Grinberg,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Cinematic Temporalities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2015)
Issac Marrero-Guillamón,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Non-Representation: Re-Imagining
Ethnographic Cinema with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2018)
網頁資料
陳界仁,〈凌遲考—創作自述〉,《伊通公園》網址: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essays_data/10/842/73(2019年12月16日檢索)
藝術新聞中文版,〈回答 2017 | 陳楸帆 V.S. 陸揚:妄想曼陀羅,穿透異次元〉,《微
文庫》網址:https://www.weiwenku.org/d/101442453(2019年12月20日檢索)
起點專訪,〈「藝術不需要艱澀,何不讓更大的群體自然進入你的世界」次世代藝
術指標陸揚特別專訪〉,《起點》網址:https://keedan.com/track/2018/06/19/keedan-special-interview-with-yang-lu/(2019年12月20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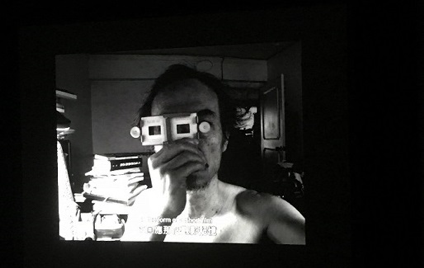
Comentarios